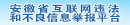疏胜祥
父亲大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我九岁那年,他五十四岁走的,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即使是最模糊的黑白照。那个年代照相是一种奢侈,父亲根本没有这个条件。但我记忆中的父亲形象依旧清晰如初:瘦高个子,驼背光头,体弱多病,经常心口痛,他是个嗜烟如命的烟鬼。
童年的家庭共有六口人,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哥和我。记忆中的父亲一直是心口痛常挂在嘴边,常常卧床不起,母亲每年夏秋换季时分,鼻子常流血不止。家中主劳力只有梅香大姐一人,哥哥还在初中读书,小姐姐芙蓉给生产队放牛,我九岁才上小学读书。
听父亲说,祖父是晚清民国期间的举人,在当时的安庆巡抚为官,好像是主管财政的。父亲九岁那年,祖父因乘船爆炸在长江里遇难,家道一落千丈,父亲随祖母外出四处要饭,后来回到老家无宅基地立足,被迫在一处停放棺材地的地方落脚安家了,筑茅屋三间。
我八岁那年的腊月,家中债台高筑,父亲是个要脸面的人,为了在年前还清债务,把家里唯一可以变卖的一头八十几斤重的年轻黑猪卖了,换得五十块钱回来还债。当夜冒着刺骨的寒风,拿着一张十元大钞,去连生叔家里还债,不料路途中被大风吹走钞票,父亲整夜提着马灯找遍整个村庄,也是没有找到。一个月之内,父亲仅有的几根毛发全白了。这年春节,父亲一直黄烟袋不离手,常常夜不能昧,愁容满面,一年过来老了十多岁。
我九岁那年荒春,家中因无劳力干活,在生产队里工分严重超支,生产队不但不分给我们家工分粮,而且还将人口粮扣掉,全家人已无粮可以糊口,面临举家断炊挨饿。父亲厚着脸皮去了邻村张老头家借了两担山芋渣回来糊口,被迫拿了这种叫“放稻薪”的高利贷(这在当时农村里是一种高利贷,以粮食为计算,即今年借100斤,明年要还150斤)。可怜父亲无力偿还高利贷,最后只有答应把梅香大姐许配给张老头家长子了。这也许是解放后少有的卖儿卖女现象了,竟然发生在我童年的家庭。
父亲是个特别严厉的人,这年初夏的一天,父亲要我在家看管一窝刚刚孵出来的小鸡,不准出去贪玩。大人们都出去干活儿去了,我被几个小伙伴喊出去劻泥巴去了,等到中午父亲回家后才发现一窝小鸡被田野里黄鼠狼跑到家里洗劫一空,我回家看见一地鸡毛,头脑一下子就晕了。父亲拿起一根桃树条,朝着我的两条小泥腿儿猛抽,那桃树条每根抽下去就是一条血痕,顿时鲜血直流,父亲满脸铁青,喘着粗气,仍不解气。我为了不让父亲更生气,一声不吭,也不躲不让,让他打个够。哪知道父亲见我无任何反抗,他更加气恼,竟然气得一病多日。这是记忆中父亲给我最严厉的一次毒打,也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父亲产生了对立情绪,或许我是提早进入青少年叛逆期吧。
记忆中的父亲常常也是个慈爱的人,每到生产队收工回家的时候,都要一把抱起我,用他那粗硬的胡子茬扎我的脸,然后还时常带些意外的惊喜。有时将在工地上吃饭特地省下的饭团,放在竹子筒里带回给我吃;有时因犁田捉些黄鳝泥鳅鱼虾之类的带回来。童年的我时常在村头翘首以待,等候着父亲回来,等候是否有意外的惊喜!这种等待成了我童年的一大幸福之事。
就在我九岁的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依然如平常一样等待着父亲的归来,猜测着父亲带给我的意外惊喜。可这次我竟然等待了父亲被村子里的大人们用竹床抬回来了,我心头感到莫名的恐慌,父亲已奄奄一息,嘴角上挂满了血迹,两脚沾满了泥巴。很多人围过来看,我魂不附体地挤在人缝里看着母亲竭斯底的哭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微弱的眼神看着我和母亲,眼角上挂着泪珠。长保叔向人们讲述父亲在干农活时,突然晕倒在泥田里大口吐血,大家立即把他抬回家中。经过简单的清洗处理,建石村长命令立马抬到白云卫生院,检查结果是胃溃疡大出血,需要手术医疗费3000元。这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了。全村人不吃不喝也无法筹齐这笔巨资。三天后父亲因无钱治病被抬回家,第三天夜里再次大吐血,惨不忍睹。至今我记忆尤新,这一幕让我童年的记忆永远成了血色。第四天午后父亲痛苦地永远闭上了双眼。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的脚丫里还沾着泥土,就这样躺在草席上永远地安睡着,满脸的蜡黄,双手攥着无力的拳头。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几度晕厥。邻居瘸婆一边帮忙我们料理父亲的后事,一边不停的嚷嚷着:“天啦,这一家子梁倒了,梁倒了,真的梁倒了…”。在建石村长的帮助下,父亲的丧事在三天内草草的办理完毕。之后的很长时间,母亲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啼哭,将我从睡梦中哭醒,我们几个儿女一个个揉着睡意蒙蒙的眼睛,无奈地看着母亲,无论姐姐如何劝慰,都不能抚平母亲的悲伤。按照乡下的习俗,丧事四十九天后,不能谈婚论嫁。邻村张老头“趁火打劫”,送来了为儿子催婚的帖子,在母亲极度悲伤之际,还未成人的梅香大姐很快不得不出嫁了。
一个虽然苦难但也温馨的六口之家,一下子就死了一个,又嫁出一个,剩下的这个家在母亲的维系下,艰难度日,苦而不散。母亲多病,家中无劳力挣工分,哥哥只能从初一的书桌上把书包捡回家了,从此扛上了锄头,成为生产队里的一名最小的社员。小姐姐芙蓉从未跨过学堂,只能做了生产队里的放牛娃。母亲根据父亲临终遗言,一定要将小儿子我送到学校,识字念书,将来好记账认工分,再也不能像父亲那样文盲睁眼瞎了。父亲离去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坐在村口的那颗老槐树下,遥望对面的山岗,遥望埋葬父亲的墓塚,心中默然的惆怅和无助。失去父亲的孩子在那个艰难的岁月是多么的孤独与凄凉!
父亲大人离开我们已整整四十周年了,我们几个做儿女都已过半百之人,父亲大人生我们养我们四个儿女,有生之年从没有享受我们一丝一毫的福分,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我们今年冬至之日为父母大人修墓立碑,以报达儿女尽孝之心。
|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
编辑: 蒋骁飞
|